中秋,携着记忆的风烟
□ 焦娟娟
前几日,单位的姐姐送一大块月饼,这块月饼,是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月饼,常听人说甘肃河西地区的人们有自己制作这种月饼的习惯,可能凉州更胜。人这一生,冥冥之中有些人有些事似乎有着不可改变的宿命,就像我作为一个河东人,也许在生命的前二十年,永远都不会想到我的生活的大部分地域会是在凉州,而在此之前,我与凉州全然陌生。我想,其实每一个节日,并不是简单的重温和复制,而是在这个节日的节点按时唤醒那些情绪,那些缱绻往事,然后去邂逅那些时光深处的人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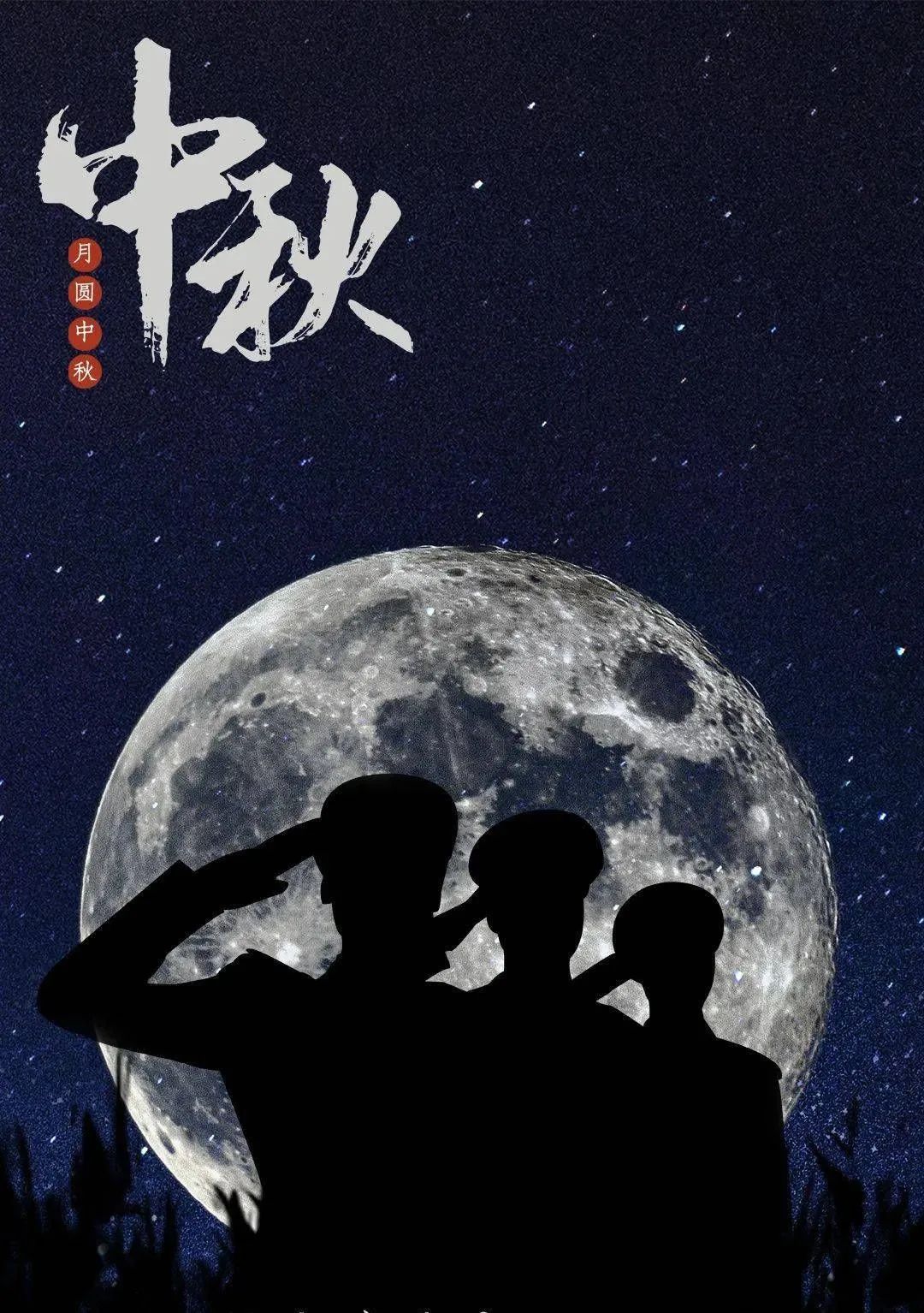
中秋临近,我便不由自由的便想起那些旧时光,还有时光深处的家乡。家乡,对于一个身在他乡的人,也许永远都是一种回不去的乡愁。在东方传统畏和崇拜,中秋尤胜。中秋节,起源于古代对月的崇拜,其最早记载于《周礼》,普及于汉代,唐朝初年定为全国性节日。据史籍记载,古代帝王多有祭月活动,日期定为农历八月十五,因为此时正是三秋之半,故名为“中秋节”。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亮节、团圆节等,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之一。文化里,很多节日节气都无不体现着农耕民族对大自然的敬而我对于中秋的认知和理解,最初是源于家乡那片土地。时至今日,那片土地给我的关于节日的力量和仪式,转化为一种生命的态度和情感,在这个特殊的节点,那些记忆深处的人和事,和着中秋的风烟,喷涌而出。我的家乡,距离天水市秦安县22公里的一个乡镇—兴丰镇,因地处山湾,故名曳湾里,兴丰在历史时期属秦州、天水县所辖,民国《天水县志》有零星记载。后随历史变迁,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曳湾梁上逐渐形成了集市,而后迁往今兴丰镇,沿用至今。

依着记忆的烟雨,我的思绪回到了很多年前。一个孩子对节日最简单的认知,无可厚非便是吃喝,中秋于我的少年时代,记忆是密密匝匝、浩浩荡荡的。进入秋天,对于一个农人来说,此时已经五谷进仓,一切都闲散了起来,自然而然的就有了空闲来准备这样的节日。记忆里,我家院子下面邻居家的园子里,有一个石槽,中秋前两三日,几乎半个庄子的人纷纷端着新粮食到石槽里捣磨,只为在中秋那天吃上用新麦子做的甜胚子。他们一边干着活一边讨论着今年的收成如何,你家收了多少袋麦子,我家打了多少袋油菜籽胡麻之类的,这项工作大多都是由母亲来完成,那一刻的他们,满脸的慈爱和温柔,似乎再也没有了满巷子追赶打骂自家孩子的凶相,若遇上一个大好天气,阳光调皮的挂在树稍上扮着鬼脸,风细细的,柔柔的,和着丰收的欢声笑语,在那个秋天的午后,烟火气荡漾在整个院子里,一切是那么的沉静和美。

母亲做甜胚子的手艺向来很好,看着母亲把磨好的新麦倒入锅内,用柴火烧热锅,不一会儿,满屋子的氤氲之气,水开后,水汽从麦子里源源不断冒出来,此时满屋子水汽弥漫,年幼无知的我们姐弟,知道中秋节要在这样的烟火气里一点一点的漫溢开来了,于是开心的像是要过年一样。片刻,母亲揭开锅盖,拿筷子夹起几粒即将黏在一起的新麦尝,把握这软硬想必是一件技术活,而母亲总会掌握的恰到好处。母亲看着软硬刚好的时候便开始起锅,把煮好的新麦盛出来晾在案板上,等晾的差不多温度的时候,装入瓷坛中,盖上盖子,最后还不忘在盖子上捂上一件衣服。发酵个两到三天,甜胚子便做好了。母亲总会算好日子,一般都是中秋节的早上便是甜胚子发酵好的时候。中秋的前天晚上,母亲也会和好两坨面,一坨是准备第二天炸油饼用的,而另外一坨,母亲反复地揉呀揉,等面揉得的足够劲道时,把面坨放入早已备好的面盆中,添水,反复搓洗,直到面坨最后只剩下面筋,再拿筛子过滤掉面糊,静置等中秋节的早上蒸面皮用。“我做甜胚子的手艺还是你婆教给我的,我也是为了你婆才反复的学,因为你婆喜欢吃甜胚子”,母亲眼里浸满泪水,泣不成声。我知道,母亲是一个称职的儿媳妇,她和祖母的感情不是母女却胜似母女,祖母和母亲两人几乎倾其一生在彼此成全,投其所好。这世间的爱,是一场场永不止息的接力。我从祖母与母亲身上深深的读懂,所有那些关于爱的叙述和表达,无不告诉我们爱更应是反哺,是传承。在爱与被爱这条路上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殊途同归。我听着母亲娓娓道来那些关于祖母的风烟,我的眼泪簌簌的流了下来,我知道,此刻的母亲,仅仅想用做甜胚子这件事,去叙述和表达她对祖母的情深几许,往事依依。那一年的中秋,我的祖母,她已经狠心的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们,留给我关于中秋和祖母最后的回忆就是祖母再也吃不下甜胚子,那一年的中秋,因为祖母离世,月亮不再那么圆月光不再那么柔软。中秋节一大早,母亲便早已在厨房里忙了大半天,炸油饼,蒸面皮,等着月色降临,父亲将水果、干果、糖果装盘,端上桌,道上茶,点烛焚香,开始祭拜月神。那一瞬,父亲沉默不语,生怕惊动了天上神仙的宁静,但一言一行尽显恭敬、周全和虔诚。我想,关于家乡的每一份情感和风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那情景那味道那风烟,一点一点的根植在我的血液骨髓里,就像家乡那片土地一样,给予我生命的情感。

湛蓝老师说“我蓦然发现童年和少年时代耳濡目染的民风民俗,是一种积蓄的力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他们润物于无声,柔韧又不可防御地与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一同生长。”是的,正是基于这种强大的原始情感和生命的力量,让我和那些和我一样身在他乡的游子,在某个特定的日子,还能有一份关于故土的牵挂,想到这里,我觉得我依然是幸福的,至少比起我们的孩子。当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出生在城市,对于他们而言,没有故乡的概念,更不会明白,故乡对于一个人那份血脉涌动的情结。对于我们的下一辈再下一辈而言,传统民俗的概念少的可怜。可见,根植在我们骨骼里的“根”元素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弱化,也许不久的将来,被节日化的民风民俗将也会流失的荡然无存,我不禁思索,当下的快生活节奏到底馈赠了我们什么,又剥夺了什么。而我又无比清醒的意识到,关于中秋,成了许许多多人遥望故乡的回忆,关于故乡的这种“根”文化无疑也是生活在城镇里面的大量农村后裔的集体回忆。关于中秋的风烟,便无意识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印在心里永远挥之不去的集体性格。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少年读时不知文中意,而今读时已是文中人。这一瞬,我强烈而又深刻的意识到,那个家乡,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而那个关于家乡的中秋,是无轮我身在何处,永远都遥想的故乡。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草木,故乡的所有风烟,都是我要用这一生我倾其所有去守护的那份血脉涌动的情结。也许只有踏上故乡的那片土地,遥望着她的脊梁,我的心便才会安稳一份,欣慰几许。

身处他乡,窗外的灯火流萤,月光像水一样洒向人间,蓦然回首,似乎在等着点什么,等风,等雨,等那个和我一样“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你,霜草苍苍虫切切,这清秋的容颜,凉中透着暖,思念里透着甜。原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多么质朴而深刻的念啊,而“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又是多么的意切切,原来,故乡对于游子而言,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殊途同归。
责任编辑:高富强
1.本文为法治甘肃网原创作品。
2.所有原创作品,包括但不限于图片、文字及多媒体形式的新闻、信息等,未经著作权人合法授权,禁止一切形式的下载、转载使用或者建立镜像。违者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3.法治甘肃网对外版权工作统一由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甘肃云数字媒体版权保护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受理对接。如需继续使用上述相关内容,请致电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联系电话:0931-8159799。
